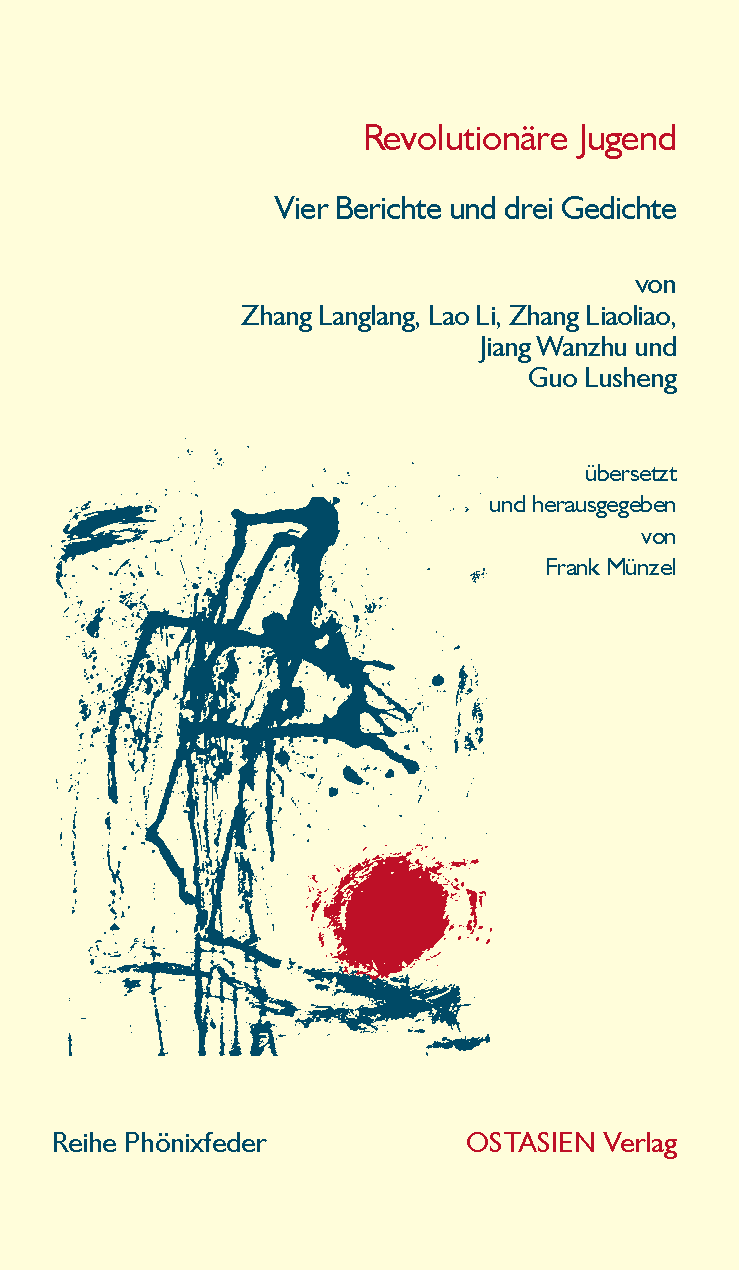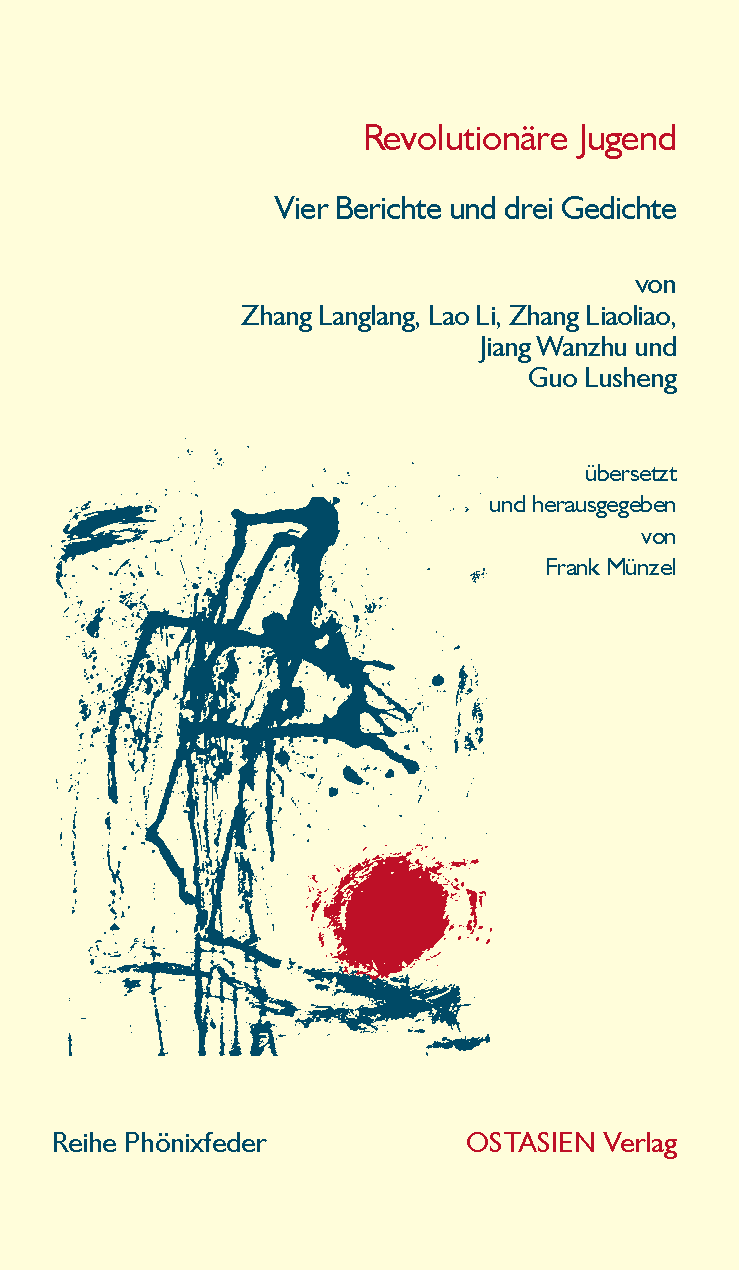终于, 把他送进了疯人院。
我们曾住在一起, 而且有一种默契, 我不认为他
疯了, 他也知道我这样认为。
他名字叫国宝, 独生子。 1975年, 家里为了他回北京, 让他在东北黑龙江兵团装疯, 病退回了北京。 虽然是装疯, 可在北京复查时, 在疯人院关了几个月, 他真的神经嘻嘻的了, 见到任何人, 只是微笑。
他出院后, 父母出于好心, 将信将疑地每天让他吃"安定"十倍的镇定剂。 我们住在一个宿舍, 他父亲多次叮咛, 让我监督他晚上的用药。
我问国宝感觉如何, 他笑着说: 如果不吃药, 我就不会这么呆头呆脑。
我于是干了一件事, 我把他的一瓶药, 扔进了垃圾箱。
他真的清醒了, 眼光也亮了。
当时, 我们共同管理一个工艺史陈列室, 多多少少, 有些值钱的东西, 什么唐三彩的瓶子, 明朝的大青花碗之类。 。 。
后来, 我们这室来了一个新人, 姓文, 叫文成。
他在一天下午打碎了一个宋磁碗, 而且还写了检查。
可他忘了有一块磁片没扫掉, 被国宝发现了。 他说,
这不是那个碗, 这是现在的景德镇出的青花。 这里边儿有鬼。 。 。
事情传出之后, 姓文的老羞成怒, 逢人就说国宝疯了, 说的全是昏话。 这话直传到其父耳中, 可是文成的编造中, 有一句真话作为支柱, 那就是说, 我使国宝停了药。 他被弄回家, 并承认了停止了用药。
于是, 一切谣言全成真的了, 国宝所说的一切, 都是疯话, 而且成为了一种饭后的笑谈。
我无法替他解释, 因为我先就是使他"发疯"的罪魁, 所以只能沉默(据说沉默是金子)。 但是, 国宝每天来上班时, 又渐渐地, 木木呆呆了, 更多的人开始拿他逗乐子, 对他调笑和愚弄。
我很想找到那块磁片, 但它早已不知去向了。 姓文的小子, 整天和领导们在一起, 他们是勾着的。
幸而, 我仍然和国宝一起上班工作, 他还不显得那么寂寞。 可那些半老不老的女人, 走进我们陈列室时, 拿腔作势的"关怀", 使他越来越深地受到了刺激。 我估计他是否也认为自己得了精神病。 她们总是说: "今天
吃药了没有? 最近感觉怎么样? 有没有觉? "而在走路的时候, 永远和他保持着五米多距离, 好象国宝会一下子把她们杀了, 而又不必负刑事责任。
"他杀人不用抵命, 因为他是疯子。 "这是那些人的口头禅。
日子就这么过去了。 直到有一天, 国宝微笑地对我说: "我停药了, 这是医生允许的。 "我很高兴, 但告诉他, 先不要对别人说, 省得。 。 。 可他没介意这个, 他总是相信人们都是极善的。 当别人问他: "今天吃药
了吗? "他就回答: "我疯病好了, 医生说可以停药, 我不吃了。 "
一下子, 好象如临大敌, 每个人都惴惴不安起来。 好象国宝被解开了他那随时可杀人的双手。 大家都唧唧咕咕的在背后议论, 都等待着那肯定会来的灾祸。
结果, 他们如愿了。
一天上午, 国宝进编辑室, 想问个什么关于文史的资料之类的事。 当时屋中只有一个叫袁园的, 刚刚怀了孩子的人, 她是从来不嘲弄国宝的少数人之一。
大概当时她因为很不容易地怀了孕, 所以很高兴,
她对国宝说: "你别在我这儿发疯啊。 "
国宝不自然地笑了笑, 推了她一下, 说: "你也开始这么说了? "可当时袁园在桌后, 是倚在椅子上, 只有两条后椅腿支着地, 而她面前又是一大堆资料,
国宝不知道。 结果她一下子摔倒了, 国宝去扶她, 她不让, 只是哭。 在这当口儿上, 管编目的王处长冲了进来, 他是那种你在街上走都得绕行的人, 我不是说他有多魁伟, 而是他脸上的肉长得不大对, 全横着。
他一见这事儿, 二话没说, 把国宝一拎, 像小鸡子一样扔到墙上。 国宝怒火上升, 拿起地上一个暖壶砸了过去, 可王处长躲过了, 又扑。
我在旁屋, 听见"轰"的一声响, 那是暖壶的碎音。 我连忙跑过去, 进了编目室时, 我只见国宝立在屋当中, 袁园坐在地上, 满眼是泪。 而王处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, 一动不动。
"怎么啦? "我大叫, 可没入理我。 忽然, 只见国宝冲出屋去。
他是去医务室了, 三分多钟, 牛医生来了, 听听王处长的心脏, 量了量血压, 说, : "没事。 "又问: "怎么搞的? "国宝紧张地悄声说: "他滑倒了, 他想抓住我, 可他被椅子绊倒了, 又正好撞在文件架上。 "
只有我相信这是实话, 可有什么用, 谁也不信。
中午吃饭时, 所有人都在说, 国宝疯了。 把一个刚怀孕的女职工踢成了流产, 处长去救援, 又被他一暖壶, 打成了脑震荡, 昏死了。
下午, 他没来。 可单位宣布了, 对他处以停薪留职的处分, 此处分到他病好为止。 并担负受害人的医药, 营养。 。 。 费用。
袁园歇了三天假, 就来上班了。 也难为她结婚四年了, 刚有了身孕。 可她听到了单位的决定, 就立刻跑过去找领导, 退还了国宝送的鸡蛋, 麦乳精。 。 。 之类的营养品。 她说: "我和国宝是开玩笑, 责任在我, 不在他。 至于他和王处长争斗一事, 我没看见。 "
可谁听她的呢? 王处长住在脑科医院, 他声称: 不开除国宝, 我没法出院。 "我受了脑损伤和刺激。 。 。 "
国宝真是没来上班, 直有两个多月, 由一个临时工替代他。
一天下午, 全处人员开会, 关于长工资问题。 正在热烈的时候, 忽然大家一下全哑然了, 我从朦胧中, 抬起眼?
国宝, 站在门口。 手里拿着一个崭新的暖水瓶。 那是他来赔偿损失的。
领导我们会议的朱处长, 环视了一下四周, 忽然, 他像武林好汉一样, 大吼一声: "你来干什么!"
国宝微笑着, 没说出什么话来。 只是嘴角动了动, 我知道, 他又吃药了。
"出去!"朱处长的火气不知打哪来的, "出去!再也不许来!你是个疯子!你知道吗!"
国宝脸色发白, 忽地直朝我走来, 把暖水瓶交给我, 转身就走了, 我看着他的后背, 好象在发着抖。
在门口儿, 他又站住了, 回过头儿来, 清晰地说: "给我长工资了吗? "
"出去!"
他走了。
结局。 单位领导决定, 把他送精神病院。 时间是我得知的当天清早。
我跑去找朱处长, 告诉他这个决定不能挽救国宝, 我说我愿意和他共同工作和生活, 我愿为他和我负责。
朱处长看了看我, "这是上级的决定。 "
我说: "我反对这个决定。 "
朱处长大叫: "你负不起这个责任!他要杀人放火, 你负责吗? 对他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!他是疯子!"
我也急了, 我说: "也把我送进疯人院吧, 要不就是他疯了, 要不就是我疯了!"
最后, 当然是我屈服了, 我不可能和这既成的事实, 去解释什么。 。 。
本来, 单位指定我们处出八个人去解送, 但除我之外, 别人都弃权不去, 各找借口。 他们一半是害怕, 另一半呢, 或许是同情。 。 。
我去。 因为我不愿那别科的五条大汉, 欺辱国宝。
他们真准备了绳子, 那绳子足以捆起一头牛来,
还有两条棍子, 本是做铁镐把儿用的。
他们通知了国宝家里, 让他来开会, 由我去稳住他, 把他哄上面包车, 如果他不肯, 就只能用暴力, 为了不对"人民残忍"。
那天天气好极了, 正是初春, 到处飞扬着柳絮, 阳光温和而又不热。 在九点差十分的时候, 国宝准时来"开会"了。 我见他穿过操场, 显得那么弱小。 他根本没注意到, 树丛后和窗户中看热闹的人们那热切的目光。 他是那么瘦和单薄, 却昂着头, 目不斜视地朝我走来。
到我面前, 似乎微笑了一下, 说: "解除对我的处分了? "
我点了点头, "上车再说吧。 "我说。
他问: "去哪儿? "
我没回答。
但他毫不怀疑地和我上了车, 他坐在靠窗的位上, 我坐在他身旁。 那些人也上车了, 坐在我们身后。 车发动了, 飞快地开出了单位。
路上, 国宝问我: "你长工资了吗? "
"长了一级"。
"以后会给我长吗? "
"那是肯定的。 "
"开什么会? "他问。
"到时你就知道了: "我应。
当我们的车, 在精神病院前转弯的时候, 国宝一下看见了路标: 往北?精神病院。 他猛然转过脸来, 问我: "是到这儿? "他脸发白了。
我点了点头。
他楞了片刻, 从手上把表摘下来。 "给家里。 "
他说, "还有钥匙。 "我能觉出后边儿人的紧张, 空气都像凝住了。
到了。 下车时国宝小声问我: "不会电我吧? 我没病。 "
我又是点头。
在门诊室, 由单位的同志们介绍了病情, 诊断为"躁狂型精神病+++"。 然后就先打了一针"强效冬眠灵"。
他开始迷迷忽忽的了, 我扶着他去洗了澡, 换了一身住院的白粗布病服。
"我会来接你的, "我说, "很快来接。 "
他最终被两个男护士架向一扇铁门, 当他们开锁时, 国宝回过头来, 一瞬间他好象全清醒了。
"来接我。 "他说, "别骗我。 "
那扇铁门关上了, 里面又上了锁。
回到单位, 朱处长等领导表扬了我, 说我"免除了一次可能伤人的事故。 "最后, 朱处长说: "我们不会让他回来的, 不会让他再惹事。 你要什么人替他的工作? "
我看着他没吭声, 我想是不是我也疯了。
"想好了吗? 让谁替? 你要谁都行。 "
"我等国宝回来。 "我说。 然后就走了, 我知道这话, 得付出多大代价, 我不在乎, 我真的要等他回来, 别人我不要。
是的, 我不在乎, 当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把一个弱者投井下石的时候, 我甚至不能成为一个阻拦者, 却几乎成了帮凶。 我一直记得那扇铁门, 当锁挂落之时, 弱小的诚实便成为过去了, 而门外, 不过是些欺着自己, 也欺着他人的人。
他回来了。
他向我走来, 握着我的手。 我们什么都说不出来, 但我们中有一个人哭了。
哭的不是他, 因为这是我的一个梦。
|